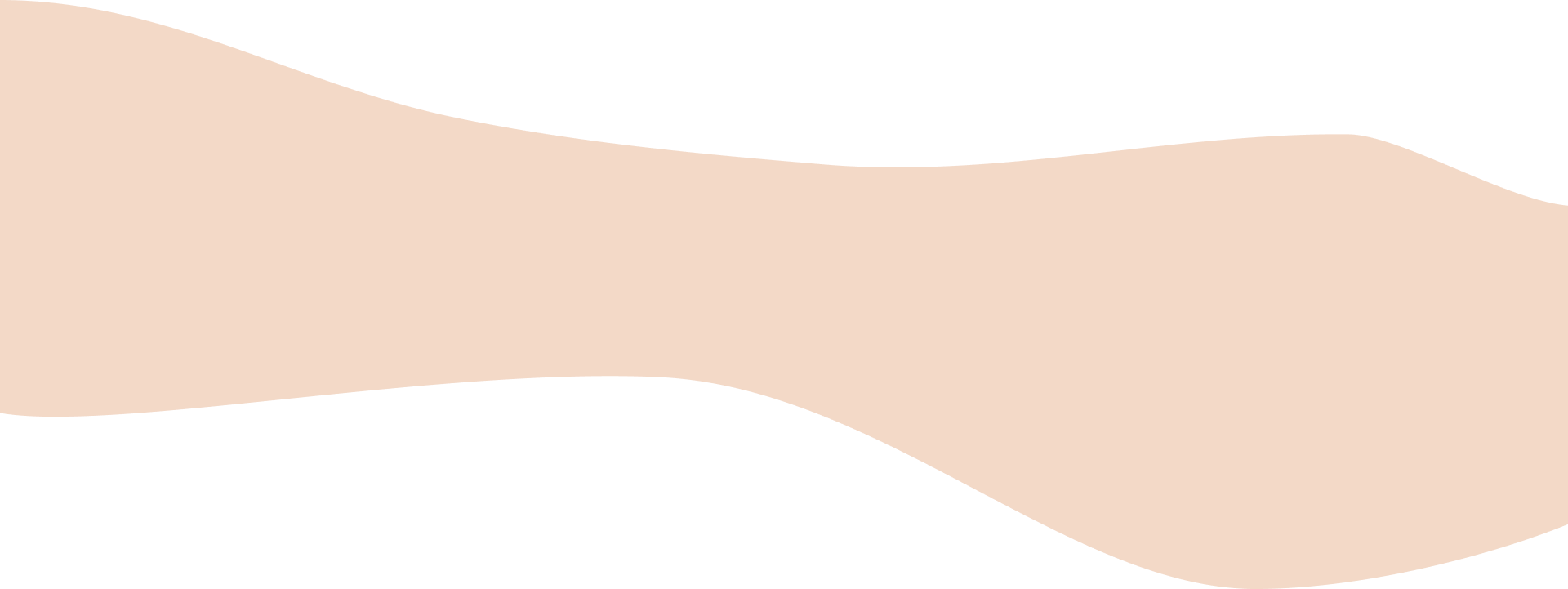童年好友阿永領著母親重遊新埠頭。
五十多年後,印尼加里曼丹那個老家什麼都不剩,只剩下屋子後面的這座山。當年接濟母親一家的舅媽說,逃難在她十七歲時爆發,親戚都到搭船去中國了,但他們沒搭到。她想繼續讀書,認清了必須以印尼人的身分活下去,就決定改成印尼姓氏。中華公會的人罵她忘本。但她還是改了,成了家族中第一個改姓的人。之後幾年,全家人終於認清事實,做不了中國人,就陸續改成了印尼姓。至於坐船至中國的印尼華人,有錢人到了中國還是有錢人,逃過了清共,但幾年後還是逃不過文化大革命清算地主的下場。
那是一個十七歲少女,試圖掌握自己命運的時代,舅媽嫁給了舅舅,一個勤奮的客家男子,後來經營金店事業,每日能賣上公斤的黃金。一說起坤甸的金店,人人都知道這家店。舅舅則是遠近馳名救濟逃難的善人。小孩子們不懂事,彼此開玩笑說,叫我媽把臉塗黑,去金店門口討錢。阿雪阿姨跟舅媽說起,當年寄人籬下,孩子們玩在一塊,他們家的孩子戒指不見了,誣賴說是她拿的。現在阿雪這個孩子變成了老年人,跟舅媽同車的時候說,她真沒拿那戒指。這個心結,到了這一刻才打開。
「我覺得房子還是以前的漂亮。」母親回到睽違了五十多年的小村子,現在都是水泥建的兩層樓透天厝,比不上以前用葉子鋪屋頂的老房子。這趟旅程,我們從坤甸到古晉,距離422公里。若是搭長途客運,大概要八九個小時。
終於看到了故鄉,母親有什麼想法呢?她說:「以後別人說亞洋岸(Andjongan)怎麼樣,我就可以回應了。」過去有人說亞洋岸、山口洋變了很多、很進步,但在她看來一點都沒有。倒是新埠頭真的變了,他們住過的房子別人整修了,原本的水溝也不見了。
加里曼丹多數說客家話,但我的外婆和外公說的卻是不同的客家話。兩個地方相隔頗遠。我的曾外公家境不錯,外婆出嫁時,送了一頭牛做嫁妝,派人牽牛牽到外公家,也就是亞洋岸。母親記得當年逃難,用很低的價格賣了那隻牛,是一隻很會生小牛的母牛。
我們到了亞洋岸,無事可做,穿金戴鑽雍容華貴的舅媽,看到市集路邊的炸香蕉,買了幾塊,雙方聊起為什麼來到這裡,一旁賣香蕉老闆的父親看著我媽說,「你家在前面。」老人說,我媽和她的父親長得很像,不用說就知道她是誰家的孩子。
「我一點也不覺得自己很像。」我母親說。但這張臉確實是回家的通行證。
用休旅車快速來回主要幹道兩次,不知道要拍什麼,只好快速下車,穿越到對面的空地,跟養豬時總會看見的山合照。不然就等於什麼都沒看到了。
「我比我媽還早離開,帶著大妹去坐車,還在河邊幫她洗澡。」因為外婆還要收些東西,沿路上有人幫忙照顧母親跟她妹妹,這才到了坤甸開金店的表哥家。但確切是哪一天走的,她完全記不得了。
「逃難的時候,我剛煮了一鍋飯,就帶在路上吃了。」我媽的童年好友阿永,如今住在坤甸近郊新埠頭。她當年十二歲,記得那天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,母親只比她早幾天離開。那是在軍事政變九三〇事件之後的事了。

母親老家只剩下一片空地。
如今不比當年,兩天就能回到他們花費了大半生才離開的地方,但也同樣充滿了各種挑戰。兩年前坤甸開了新路,稍微不那麼顛簸,但我暈車吐了。忍不住想起鹿野忠雄和蕃人進山,該不會就是這種感覺吧?(另一個可能是,到了現在,印尼和馬來西亞客家人還是用蕃人這個詞,絲毫沒有改變。)身為印尼當地人的阿姨,得了病毒型腸胃炎。下午開始拉肚子,晚上就發冷送醫。我們其他人也拉肚子。後來檢討應該是吃了這三樣東西:炸香蕉、用鏽刀削過的鳳梨、還有叔公家的茶水。
我們從亞洋岸往坤甸的方向移動,到了新埠頭。明明沒有事先約好,但巷口聊天的幾個人,聽見有人來了,大家都紛紛聚集過來,一眼就認出了我母親。赤裸著上半身的男生是裁縫,做工的阿榮現在也不做工了,就待在村裡晃晃。沒跟人結婚卻生下三個女兒的阿永,傳言說她做的是妓女,但大家都說她的日子比以前舒服了。
都說好心有好報,但接濟母親一家人的舅媽家,終究因為樹大招風,就算賄賂了警察,總是有人在店門口鬧事,不得已搬走換店面,生意自此一落千丈,幸好她的孩子都大了,到了別的地方去,甚至是別的國家。他們夫妻倆和雇用了三十年的幫手,守著坤甸偌大的房子,大得足以讓所有家族成員同時入住,但大家工作忙碌,節慶休假的時間不一,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團圓。
文/陳又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