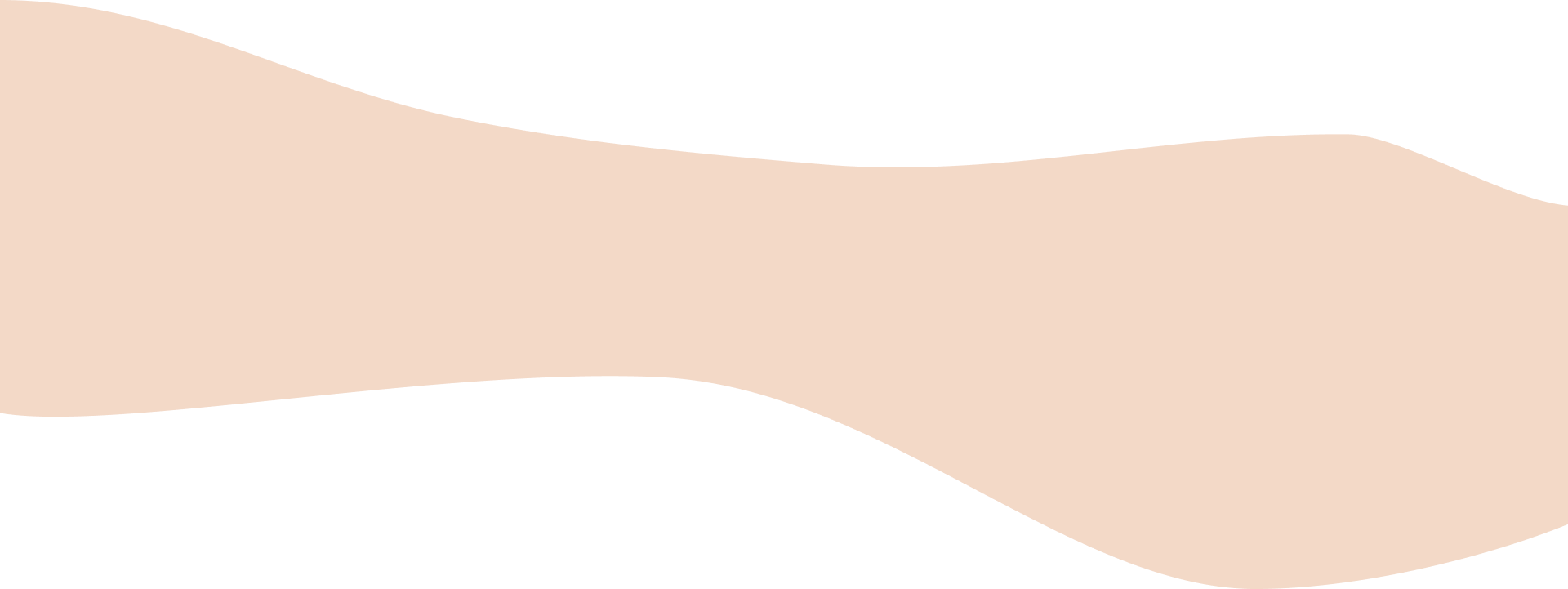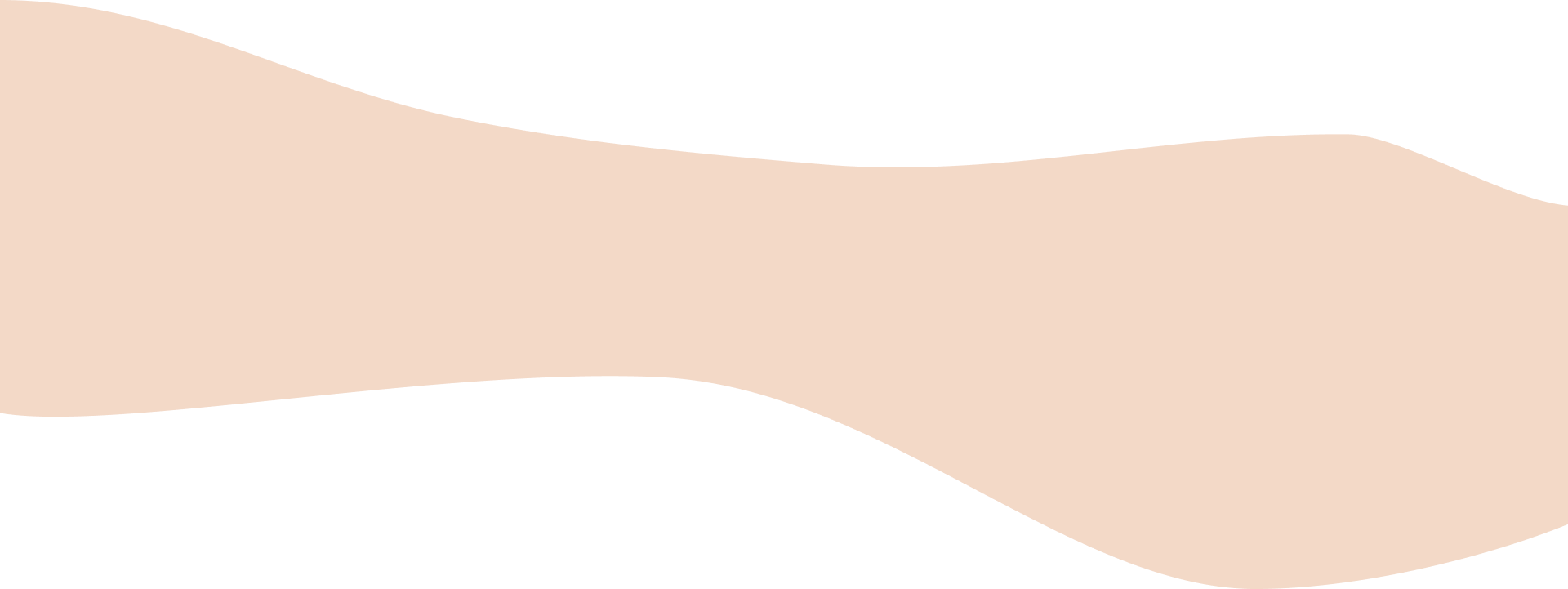新住民女性心理衛生
新住民離開家鄉來到台灣,面對陌生環境、生活日常,語言不熟悉及無法敘說的思鄉情緒,如何好好生活已然是個議題,何況自我發展及生涯展翅飛翔。移居者逐步融入當地生活的過程中,若缺乏家人及朋友的支持、相關社會服務的陪伴,可能面臨心理健康的挑戰。WHO(2023)在Mental Health of refugees and migrants: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nd access to care報告中提及,有心理健康照顧需求者未能獲得服務的情況在全球普遍存在,但在移民和難民群體中尤其嚴重;其中,移民者比在當地出生的人少了40%的機會接受心理衛生服務。近20年已有研究針對新住民在心理衛生議題進行探究;例如新住民女性容易因為不適應移居生活及溝通障礙導致情緒困擾(林妍如、蕭文彬,2009),Lien et al. (2021)研究發現,台灣新住民女性結婚年數越長,憂鬱情況越惡化;婚姻移民者不了解應該到哪裡尋求心理衛生服務,迷航於複雜醫療系統中(鄧旭茹,2023)。新住民女性認為遭受醫療人員的歧視態度,包含談話時間較短、態度不耐煩等差別對待(鄧旭茹,2023;張雅晴,2021)。儘管目前已有相關的方案介入提供新住民的各項服務,但是Luo et al. (2022)的一份系統性文獻回顧指出,改善移民女性心理衛生的介入方案的效果有限,目前的方案大部分以團體方式進行,但成果不顯著。綜合而言,新住民女性因為多重弱勢情境及缺乏社會支持系統,成為心理衛生議題的高風險群體。新住民女性的心理健康議題,不僅僅是心理層次的需要,同時也呈現出隱於性別、族群、社會文化及生活適應等交織性議題,誠如Crenshaw (1991)針對族群與女性生命議題提出了交織性(intersectionality)概念,文章中針對黑人女性面臨結構、政治及文化代表性的交織性,產生與白人女性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,交織從屬性(intersectionality subordination)是不利因子加諸在現有脆弱特質上的必然結果,導致壓迫、限制及不平等,唯有覺察交織性,才可能了解少數群體女性被邊緣化的多重壓迫經驗。由於新住民女性同時具有性別、種族、文化、移居、社會經濟地位等多元特質,以交織性理解其生活處境已成為主流的服務策略(Knaifel & Rubinstein, 2024)。交織性的議題為新住民女性帶來的不僅負面結果,也可能產生機會與資源。Knaifel and Rubinstein (2024)研究發現,移民女性雖然因為多重交織壓迫面臨污名及排除,包含經濟困境、性別歧視與文化面向,但這樣的交織性也同時產生個人成長的契機,她們發展出韌性,成為生活經驗知識的專家,以互助團體及社會倡議等策略相互支持,展現出相當的能動性。然而,林津如(2020)以後殖民女性主義觀點評論台灣主流文化以種族中心的方式,凝視來自異文化的新住民女性,抱持中產階級自由戀愛的價值觀恣意評論新住民女性婚姻選擇,無視新住民女性在婚姻適應歷程中展現的適應歷程,習慣以「我高你低」的帝國主義姿態將新住民女性視作需要協助的弱勢群體。筆者訪談新竹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陳佳芬督導,她分享關於新住民心理衛生的實務觀點,陳佳芬督導提及,新住民心理衛生重點不應該只關注在「外在」提供怎麼樣的服務,而是應同時思考如何培力她們發展內在能力,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建構真正有效的心理衛生策略。例如,當新住民碰到問題時,不是新住民問了一個問題(Q1),我們只針對她的問題回答(A1)那麼的「直球對決」,而是當新住民提出了一個問題,我們可透過專業的脈絡及新住民的生活經驗累積,交織性議題的分析與多面向服務的介入,持續陪伴新住民們除了解決問題,更理解自己身心狀態及生活環境議題,促使新住民們自我發展及發展問題解決能力。在心理衛生的服務上,可培力新住民成為心理衛生的關懷人力,例如讓新住民通譯接受心理衛生知能訓練,在專業者適當的督導下,發揮超越「如實翻譯」的能力,以新住民母國語言提供新住民姐妹心理支持與陪伴,運用熟悉的語言進行互動,能更理解服務對象的處境及心理需求。總結來說,服務提供者必須看見新住民女性的多重交織性,肯認其獨特的服務需求。同時,新住民女性並非只是被動的服務接受者,透過培力新住民女性自我發展及群體互助能力,超越社會對新住民女性的歧視想像,才是新住民女性心理衛生議題的長期發展策略。作者: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張菁芬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衛生福利所 博士生 張雅晴參考文獻林妍如及蕭文彬 (2009)。外籍配偶醫療及社會需求調查- 探討台中市與雲林縣外籍配偶之醫療與社會支持網絡。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研究報告。林津如(2020)。性別與種族、階級和文化的交織-後殖民女性主義。顧燕如 (主編),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. 貓頭鷹出版。張雅晴(2021)。新住民女性的生命經驗─ 以照顧精神障礙者的觀點為例 [碩士論文,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]。鄧旭茹 (2023)。新住民及其在臺家庭成員之醫療需求、困境及協處機制之研究。 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報告。Crenshaw, K. (1991). Mapping the Margins: Intersectionality, Identity Politics,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. Stanford Law Review, 43(6), 1241-1299.Knaifel, E., & Rubinstein, L. (2024). Intersectionality and Caregiving: The Exclusion Experience and Coping Resources of Immigrant Women Caring for a Family Member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.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, 0(0), 1-15. https://doi.org/DOI: 10.1177/10497323241271996Lien, M. H., Huang, S. S., & Yang, H. J. (2021). A pathway to negative acculturation: marital maladjustment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ngth of residenc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. BMC Women’s Health, 21(190). https://doi.org/https://doi.org/10.1186/s12905-021-01334-0Luo, Y., Ebina, Y., Kagamiyama, H., & Sato, Y. (2022).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immigrant women's mental health: A systematic review.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, 32, 2481-2493. https://doi.org/DOI: 10.1111/jocn.16378